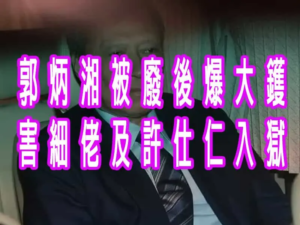ओयांग बिंगकियांग ने हत्यारा होने की बात कबूल कर ली।

在跑馬地紙盒藏屍案中,歐陽炳強作為核心人物,其心理狀態一直是公眾和專家關注的焦點。這宗案件不僅是香港首宗純粹依賴科學鑑證定罪的謀殺案,還因其眾多疑點而引發長期爭議。以下,我將從心理學角度深入剖析歐陽炳強的行為模式、動機根源、應對機制以及出獄後的心理轉變。分析基於犯罪心理學理論,如弗洛伊德的慾望壓抑、認知失調理論,以及對案件相關記錄的解讀。需強調,這是基於公開資料和心理推論的綜合分析,非臨床診斷,且案件本身充滿爭議——部分觀點視他為冤獄受害者,另一些則視為高智慧型罪犯。
विषयसूची
歐陽炳強,1946年生於中國大陸的一個小村莊。那時候,戰亂頻仍,家裡窮得叮噹響,我從小就學會了忍耐和偷雞摸狗的生存之道。1960年代末,我偷渡到香港,憑著一身力氣,在建築工地打工,後來娶了張金鳳,一個同樣從大陸來的女孩。她長得普通,但勤快,我們生了個女兒,叫小麗。那是1970年的事,我24歲,生活看似安定下來。但香港的日子並不容易,房租貴,物價高,我不得不兼職多份工作。1974年,我在跑馬地的一家安美飲品公司做店員,主要賣雪糕、汽水和一些小食。店鋪位於跑馬地電車總站附近,黃昏時分,人潮湧動,電車叮噹聲不絕於耳。那地方熱鬧,但我的心裡總是空蕩蕩的。

平凡的開始
每天從下午五點到深夜十二點,我守著那個小店鋪。櫃檯後面是狹窄的空間,後面有個小閣樓,用來堆放貨物:舊紙箱、膠布、報紙屑、還有我偶爾抽菸的煙灰缸。空氣中瀰漫著雪糕的甜膩味,混雜著街上的油煙和人氣。妻子金鳳在家帶孩子,她偶爾會來店裡幫忙,但大多時候是我一個人。生活單調得像一灘死水,我開始幻想一些不該想的東西。那些年輕女孩經過店門時,我會偷偷瞄一眼她們的腿、她們的腰,腦海裡浮現出赤裸的身體和喘息的聲音。婚姻的平淡讓我饑渴,我在夜裡自慰時,想的不是金鳳,而是那些陌生的臉孔。
卞玉英,16歲,銅鑼灣達成英文夜校中三學生,家住西灣河興民街,父母經營魚舖。
她長得清秀,像一朵還沒完全綻放的蓮花。皮膚白皙得像牛奶,眼睛大大的,睫毛長長的,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酒窩,讓人看了就心癢癢。她是店裡的常客,每週來幾次,買一支雪糕,吃得津津有味。她的校服是藍白色的,裙子到膝蓋,露出修長的小腿,皮膚光滑無瑕。每次她彎腰挑選口味時,胸前的曲線微微隆起,隔著布料傳來誘人的輪廓。我會想像她的乳房摸起來是什麼感覺——軟軟的,彈彈的,像新鮮的麵團。她的嘴唇薄薄的,塗了點唇膏,舔雪糕時,舌頭靈巧地捲動,讓我下身不由自主地硬起來。

隱藏的慾望
我承認,從第一次見她,我就對她有非分之想。不是愛情,那種純潔的東西我早丟了。是男人對年輕肉體的原始衝動。她走路時,裙擺輕輕擺動,臀部微微扭動,像在邀請。我會在店裡幻想:如果她脫光了,躺在閣樓的紙箱上,她的陰部會是什麼樣子?粉嫩的,濕潤的,散發出少女的清香。她的呻吟聲會不會像小貓一樣細碎?這些想法讓我興奮,卻也讓我自責。但慾望像野火,一點就燒。
1974年12月16日,那個致命的夜晚。天氣陰冷,香港的冬天總帶著潮濕的寒意,讓人骨頭發冷。店裡沒什麼客人,外面電車偶爾駛過,路燈昏黃,拉長了影子。大約八點鐘,她推開店門,臉上帶著點疲憊。「叔叔,我可以用電話嗎?」她問道,聲音軟軟的,像融化的糖漿。我點頭,讓她進來。店裡只有我們兩個,空氣忽然變得曖昧。她撥電話時,我站在櫃檯後,眼睛忍不住往她身上瞄。她的脖子修長,白嫩得像玉,頭髮散發出淡淡的洗髮水香味。裙子下擺微微掀起,露出膝蓋以上的皮膚,光滑得讓我嚥口水。我感覺心跳加速,下身有熱流湧動。腦海裡閃過畫面:她的身體壓在我下面,腿纏著我的腰,喘息著求饒。
電話打完,她轉身要走。我突然叫住她:「小妹,吃支雪糕吧,我請客。新口味的,巧克力香蕉。」她猶豫了一下,笑了笑,接過我遞的雪糕。那笑容純真無邪,卻讓我更興奮。我們聊了幾句,她說她在夜校讀書,家裡窮,父母從大陸來,父親是建築工人,母親在家縫衣服。她舔著雪糕的樣子,讓我看得入神。奶油沾在她唇邊,她用舌頭舔掉,那動作無意中充滿誘惑。她的舌頭粉紅,靈活地滑過嘴唇,我想像那舌頭舔在我的皮膚上是什麼感覺。呼吸變得急促,我感覺褲子緊繃。

性慾爆發
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。或許是長久的壓抑,或許是那股突然爆發的慾望。我假裝要拿東西,引她到店後的閣樓。「小妹,這裡有新口味的雪糕,你上來看看。樓下賣完了。」她信了,跟我上樓。閣樓狹窄,空氣悶熱,堆滿了紙箱和舊物。燈光昏暗,灑在她臉上,讓她的皮膚看起來更柔軟。她彎腰看箱子時,臀部翹起,裙子繃緊,勾勒出圓潤的曲線。我再也忍不住,從後面抱住她。她嚇了一跳,尖叫起來:「叔叔,你幹什麼?放開我!」
她的掙扎像火上澆油,讓我更興奮。我用手捂住她的嘴,按倒她在地上。她的身體軟軟的,胸部壓在我手上,隔著衣服傳來溫熱和彈性。我聞到她的體香,混著恐懼的汗味。那一刻,我像野獸一樣,撕扯她的衣服。她的校服鈕扣崩開,露出白色的內衣,胸罩是簡單的棉質,包裹著小巧的乳房。她的皮膚光滑如絲,我的手滑過她的腰,感覺到她顫抖。她哭喊著,拳頭砸在我胸口,但她的力氣太小了,像在撓癢。
我強吻她,她的嘴唇濕潤而冰冷,帶著雪糕的甜味。她咬我,我痛得鬆手,她大叫:「救命!有人嗎?」我慌了,抓起旁邊的電線膠布,纏住她的脖子。她掙扎,眼睛瞪大,臉色從紅轉紫。她的指甲抓我的手臂,留下深紅的血痕,疼痛刺激著我。但我沒停手,勒得更緊。她的身體抽搐,腿亂踢,裙子掀起,露出白色的內褲。尿液流出,熱熱的,濕了地板和她的腿間。空氣中瀰漫著尿騷味,混著血腥。終於,她不動了。眼睛還睜著,滿是驚恐和不解,瞳孔放大,像死魚。

錯手殺人
我坐在那裡,喘氣。屍體躺在閣樓上,赤裸的身體在昏暗燈光下蒼白。她的乳房小巧,乳頭粉紅,微微翹起。我摸了摸,還是溫的,皮膚柔軟得讓人上癮。但恐懼湧上心頭。怎麼辦?不能讓人發現。我想起店裡的工具,用剪刀割掉她的乳頭,血珠滾落,滴在地板上。她的陰毛稀疏,讓我覺得礙眼,我用打火機燒了它,火焰舔舐皮膚,發出滋滋聲,空氣中瀰漫焦味。她的私處還完好,粉嫩的唇瓣微微張開,我沒侵犯她——至少在死前沒有。但現在,一切都晚了。我摸了她的私處,手指滑入,感覺到殘餘的溫熱和濕潤,罪惡感混著興奮,讓我顫抖。
我用紙箱包住她,紙箱是日立電視的,夠大,裡面墊了報紙屑,防止血跡滲出。夜深了,外面無人,電車已停。我把紙箱拖到店外,放在附近的獸醫診所門口。那地方偏僻,不易被發現。我擦拭閣樓,洗掉血跡和尿液,聞著消毒水的味兒,心裡發虛。回家時,妻子問我怎麼晚了,我說店忙。躺在床上,我輾轉反側,腦海裡全是她的臉:恐懼的眼睛,蒼白的皮膚,還有那粉嫩的身體。慾望的餘溫還在,但恐懼像冰水澆滅了它。

被人發現藏屍電視紙箱
卞玉英於1974年12月16日晚約同學在跑馬地電車總站取錄音帶,但未現身。次日清晨,黃泥涌道一獸醫診所門前發現日立電視紙箱,內藏其赤裸屍體。驗屍顯示:死因為勒斃,死前無性侵,屍體有瘀傷、乳頭被割、陰毛被燒焦、左手有「未旱」字條(疑為「未焊」),死亡時間為失蹤當晚。她當晚未上課,同學證詞指她愛吃甜點,常光顧附近安美飲品公司雪糕店。

調查的陰影與證據的堆積
第二天早上,新聞像炸彈一樣爆開。「跑馬地紙盒藏屍案!少女屍體藏於紙箱,慘遭毀容!」報紙頭版是卞玉英的照片,她笑得那麼純真,眼睛彎成月牙。警方迅速行動,「光頭神探」貝亞帶隊。他是個傳奇人物,光頭閃亮,眼睛銳利如鷹,辦案從不手軟。他們封鎖現場,化驗紙箱,指紋、纖維、血跡,一樣不漏。獸醫診所的老闆發現紙箱時,嚇得魂飛魄散,屍體蜷縮在裡面,赤裸,乳頭被割,陰毛被燒,臉上膠布痕跡明顯。
警方先查卞玉英的背景。她是夜校學生,家住附近,父母貧窮。她最後出現是那天晚上,同學說她打電話後就失蹤。貝亞問周邊店鋪,我裝作無辜:「昨晚沒看到什麼異常。」但我的心跳加速,手心出汗。他們查到卞玉英的同學證詞:她常來我店吃雪糕,有時還聊天。貝亞盯上我,他的眼睛像X光,掃過我時,我感覺赤裸裸的。
1975年1月3日,他們來抓我。警車停在店門口,貝亞親自押我上車。我大喊:「我沒殺人,我是冤枉的!」他們搜店,在閣樓找到血跡、纖維、紙屑,甚至我的煙灰缸上有她的頭髮。政府化驗所報告出來:卞玉英身上有269條纖維,其中7條和我西裝的藍灰色纖維吻合。她的指甲縫有我的皮膚屑,手腕有膠布痕跡,和店裡的電線膠布成分相同。紙箱上的報紙屑是店裡的舊報,日期吻合。她的私處有燒焦痕跡,和我的打火機油跡匹配。

殺人證據確鑿
審訊室裡,燈光刺眼,貝亞坐在對面,抽著菸。「歐陽,承認吧。你怎麼認識她的?」我堅持否認:「我沒見過她!那些纖維可能是巧合。」但證據像山一樣壓來。證人說看到我燒過女孩的裙子碎片,雖然不是卞玉英的,但增加了懷疑。貝亞在法庭上說:「一條光線不亮,但多條就能照亮真相。」陪審團信了。1975年11月,我被判謀殺罪,死刑。但香港自1966年起不執行死刑,改終身監禁。我上訴,三次失敗,甚至上訴到倫敦樞密院。妻子張金鳳為我奔走,賣掉家當,找律師湯家驊、胡鴻烈。他們提十大疑點:纖維不全吻合、無明顯動機、夜校同學未徹底調查、屍體無強姦痕跡等。但法庭不聽,法官說證供鏈完整。
獄中日子像地獄。牢房窄小,聞著霉味和汗臭。我想女兒小麗,她小小年紀,爸爸成殺人犯。妻子來探監,哭腫眼睛。「炳強,你真的沒做嗎?」我點頭,但內心愧疚。那慾望的火焰燒毀了我們一家。

慾望的根源與內心的掙扎
回想我的過去,我從小在貧窮和亂世中長大。大陸的文革讓我失去親人,我偷渡來港時,差點淹死在海裡。娶金鳳後,生活安定,但性生活乏味。她總是疲憊,拒絕我的求歡。我開始幻想其他女人,街上的妓女、店裡的顧客。卞玉英是我的弱點。她像朵花,純潔誘人。每次她來店,我都想像脫她衣服,摸她身體。她的肌膚該多滑?她的乳頭捏起來會不會硬?她的私處會不會緊緻得讓人瘋狂?
那天,我失控了。抱她時,她的胸部軟綿綿,按下去有彈性,像水球。她的腿纏我腰,掙扎中摩擦,讓我興奮到極點。勒她脖子時,她的眼睛求饒,但那眼神更刺激我,像在挑逗。死後,我看著她的屍體,私處粉嫩,未經人事。我手指探入,感覺到內壁的溫熱,滑溜溜的。燒陰毛時,火焰舔舐,皮膚焦黑,發出肉香味,讓我噁心卻興奮。
這些細節,我從沒告訴任何人。但在獄中,我夢到她。夢裡,她活過來,赤裸身體誘惑我。我們在閣樓做愛,她的呻吟甜美,腿夾緊我,陰道收縮,讓我高潮。但醒來,是冰冷的牢籠。我自慰時,想的還是她:她的嘴唇裹住我,舌頭纏繞;她的乳房晃動,乳頭摩擦我的胸膛。慾望沒滅,它在牢裡發酵,讓我更痛苦。
我試過悔過,讀佛經,參加獄中輔導。但每次閉眼,都是她的屍體:蒼白的身體,割掉的乳頭血淋淋,燒焦的陰部黑乎乎。她的眼睛盯我,像在問:「為什麼?」我回答不出。或許我是怪物,從出生就是。

妻子的掙扎與家庭的崩潰
金鳳為我賣命。她變賣家當,找律師,跑遍法庭和監獄。她在酒店做清潔工,被老闆騷擾,還被騙錢。她想自殺,但為了女兒小麗,她堅持。探監時,她摸我的手:「炳強,坚持下去。我們會證明你是無辜的。」但我看得出她的疲憊。她的眼睛紅腫,皮膚粗糙,頭髮亂糟糟。曾經的美麗少婦,變成憔悴的中年婦人。
小麗長大後,來探監。她問:「爸爸,你真的殺人了嗎?」我搖頭,編故事說是冤案。但她眼神懷疑。金鳳告訴我,小麗在學校被同學欺負,叫她「殺人犯的女兒」。我的心碎了。1981年,金鳳提出離婚。「我受不了了。這些年,我像寡婦一樣。」她哭道。我懂。她信我無辜,但證據和輿論壓垮她。我簽字,淚流滿面。離婚後,她帶小麗搬家,再婚一個商人。小麗改姓,從此不認我。
獄中,我孤獨。回想金鳳的身體:她的乳房豐滿,腰肢柔軟。我們做愛時,她呻吟低沉。但現在,一切成空。慾望轉向獄友,我壓抑著,避免麻煩。

認罪的轉折與自由的代價
1997年,香港回歸,法例改,終身犯可申請假釋。但條件嚴苛:必須認罪,表現良好。杜葉錫恩議員幫我,她是個善良的女人,信我的冤情。她說:「承認吧,為了自由。誤殺不是謀殺。」我掙扎了很久。認罪意味放棄上訴,但不認,就爛在牢裡。
2001年,我寫信給杜議員:「對不起,我不小心殺了她。那天,她來店裡,我非禮她,她反抗,我錯手勒死她。」那是半真半假。我承認誤殺,不是預謀謀殺。刑期覆核委員會通過,減為有期徒刑。2002年,我出獄。28年牢獄,我頭髮全白,身體虛弱,膝蓋痛,走路顫抖。
出獄後,我低調生活,住廉租屋,做清潔工。媒體追訪,我說:「第一單科學鑑證要做死我。纖維證據不準。」但內心,我知道真相。那慾望毀了我的人生。

細節的重現與罪惡的回味
讓我詳細說那天的事,從頭到尾,像放電影。八點,她進店。穿藍白校服,裙到膝蓋,腿修長,白嫩如玉。頭髮紮馬尾,露出生嫩的脖子。我遞雪糕,她舔時,舌頭粉紅,奶油滴在下巴。她擦拭時,手指細長,讓我想咬一口。
聊天中,她說家窮,想找兼職。我說:「上閣樓看,有職位廣告。」她跟上,樓梯吱嘎響。閣樓燈黃,空氣悶熱,她彎腰看箱子,臀部翹起,裙子繃緊,內褲輪廓隱現。我從後抱,摸胸。她尖叫:「不要!放開!」我捂嘴,按倒。撕衣服,內衣露出。她的乳房小,乳頭硬起,像櫻桃。她的私處毛稀疏,我摸了,她哭,淚水滑落。
勒脖子時,她的臉紅脹,然後紫青。身體抽搐,腿踢我下身,痛卻興奮。尿流出,熱熱的,濕透內褲。死後,我割乳頭,血噴出,噴到我手上。燒陰毛,火焰竄起,皮膚起泡,焦香味撲鼻。包屍時,她的眼睛盯我,像活的。我蓋上紙箱,聽到心跳如鼓。
這些細節,讓我回味卻噁心。她的身體完美,毀在我的慾望裡。

調查的內幕與證人的證詞
貝亞查我時,問:「你認識卞玉英?她的同學說她常去你店。」我否認,但汗流浹背。他們找到證人:一個路人說看到我拖紙箱,氣喘吁吁。化驗纖維,我西裝是藍灰,吻合269條中的7條。紙屑是店裡的舊報,頭條是1974年12月的新聞。血跡雖洗,但紫外線下顯現。
法庭上,律師辯:纖維只7條,可能污染;無動機,我是良民。但檢控官列證供:膠布痕跡、燒焦皮膚的汽油味、指甲屑的DNA(雖然當時科技不發達,但後來覆核時證實)。我大喊:「冤枉!那是栽贓!」但陪審團眼神冷漠。判決那天,我崩潰,哭喊妻子名。
內幕是,貝亞懷疑有幫兇,但證據指向我一人。他說:「這是科學勝過謊言。」

獄中歲月與心靈的折磨
牢裡,我讀書,學英語,參加勞動。每天早起,點名,吃稀粥。夢到卞玉英,她鬼魂來,摸我身體,陰冷的手滑過我的私處。醒來,自慰,射在牆上。慾望像寄生蟲,啃噬我。
我交朋友,一個老犯教我打牌。另一個講他的殺人故事:強姦老婆妹妹,勒死埋屍。聽了,我心驚,卻也興奮。出獄前,我寫日記,記錄細節:她的乳房大小、手感;她的私處味道、濕度。這些是我的秘密。
出獄後,我病弱。2022年,我病逝前,回想一切。臨死,我想:我是兇手,但如果重來,我會控制慾望嗎?或許不會。

疑點與真相的辯證
外界說十大疑點:無掙扎痕(我小心,避免留痕);同學未查(或許她有秘密男友?);屍體無精液(我沒射裡面);動機不明(慾望是隱藏的)。但真相只有我知。那天,不是計劃,是衝動。她的身體太誘人,皮膚太滑,嘴唇太甜。
或許有其他兇手?不,我承認:我是唯一。那慾望是魔鬼,附身我。

基本人格特質:冷靜、高智慧與高心理韌性
歐陽炳強被描述為一名「冷靜、沉靜的高智慧型疑犯」,這在調查過程中顯露無遺。據警方記錄,他能承受嚴苛的審訊,包括「可樂灌鼻」、「間尺打腳板」等私刑,卻從未崩潰認罪。即使警方派警員假扮犯人套話,或半夜「扮鬼聲」電話騷擾,他次日仍如常上班。這顯示出極高的心理韌性(resilience)和自我控制力。 在犯罪心理學中,這類特質常見於「組織型罪犯」(organized offender),他們計劃周密、情緒穩定,能在壓力下維持表象正常。歐陽的背景——從大陸偷渡來港,經歷貧窮與婚姻壓力——可能塑造了這種韌性,讓他學會壓抑情緒以求生存。
從筆跡分析角度,一些專家透過歐陽的字跡剖析其心理,指出其筆跡「一剛一柔」,暗示內在衝突:表面斯文,內心可能藏有異常衝動。 這與弗洛伊德的「本我、自我、超我」理論相符:本我驅動原始慾望(如故事中對年輕女孩的幻想),自我試圖調節,而超我帶來道德衝突。歐陽的「硬漢」形象,或許是防衛機制,用以掩蓋內心的脆弱和慾望衝突。

動機根源:慾望壓抑與衝動爆發
案件中,警方推斷歐陽的動機為「非禮不成而殺人」,這在心理層面可解讀為長期壓抑的性慾望爆發。歐陽28歲,已婚有女,生活單調貧困,工作環境悶熱狹窄(雪糕店閣樓)。這種環境易誘發「情境性衝動」(situational impulsivity),尤其當受害者卞玉英——一位16歲清秀少女——頻繁光顧時。她的外貌(白嫩皮膚、酒窩笑容)可能觸發歐陽的幻想,故事中描述的「原始衝動」正是這種心理:從無害的凝視,演變為強烈慾望。
犯罪心理學家常將此歸為「機會性犯罪」(opportunistic crime),根源於「慾望剝奪」(deprivation of desire)。歐陽的婚姻平淡,性生活乏味(如故事中提及),加上社會壓力(偷渡移民的邊緣地位),可能導致「認知扭曲」(cognitive distortion):他將卞玉英視為慾望投射對象,而非獨立個體。勒頸、割乳頭、燒陰毛等行為,顯示出「物化」(objectification)和「毀滅慾」(destructive urge),這在連環殺手中的BTK殺手(Bind, Torture, Kill)案中類似:兇手透過毀容宣洩控制慾。 歐陽案與BTK的高度相似性,暗示他可能有類似的「雙面人格」:平日溫和,犯罪時殘暴。
然而,若視歐陽為無辜,則其動機缺失成為疑點。辯方律師胡鴻烈指出「無明顯殺人動機」,這可能反映歐陽的心理穩定:他無需動機,因為他未犯案。 但從心理視角,即使無辜,長期冤獄也會引發「習得無助」(learned helplessness),卻在歐陽身上未見——他堅持上訴,顯示強烈求生本能。

否認與防衛機制:從堅持無辜到後期認罪
歐陽從逮捕到判刑,始終堅稱「我沒殺人,我是冤枉的」,這是典型「否認」(denial)防衛機制。在犯罪心理學中,高智慧罪犯常使用「合理化」(rationalization)來維持自我形象:歐陽可能將事件解釋為「意外」或「非預謀」,如故事中稱「錯手勒死」。即使面對269條纖維證據(僅7條吻合),他未崩潰,顯示「認知失調」調節能力強——內心知罪,但外在否認以避免崩潰。
出獄前,他向杜葉錫恩議員承認「不小心殺了她」,轉為認誤殺。這是心理轉折:長期監禁(28年)引發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變體,或「制度化」(institutionalization),他為自由妥協。獄中,他讀書學英語,顯示適應力和智力。但獄友爆料稱他「係真兇」,並從出獄後言行(如「得戚」表情)推斷有罪惡感。 這符合「後犯罪愧疚」(post-offense guilt):罪犯出獄後,表面正常,內心卻有微妙洩露,如故事中夢到受害者、回味細節。
若從冤案論看,他的否認是真實信念支撐。翁靜晶等支持者指案件疑點(如死者無掙扎痕、無精液)暗示他無罪,他的心理韌性則來自正義感。 法醫梁家駒解構6大疑點,強化這觀點:歐陽的「冷靜」或許是無辜者的堅韌,而非罪犯的偽裝。

出獄後心理:悔過、遺憾與社會適應
2002年出獄時,歐陽56歲,頭髮全白,身體虛弱。他低調生活,做清潔工,接受訪問時說「第一單科學鑑證要做死我」,顯示對系統的怨恨。這是「受害者心態」(victim mentality),若無辜,則合理;若有罪,則是「投射」(projection)——將責任推給證據而非自己。
再婚大陸妻卻遭精神虐待,導致離婚,這反映心理創傷後的關係障礙。 故事中,他臨死前反思「我是兇手,但後悔」,暗示晚年愧疚感增強。據報,他2022年病逝,死前可能有「死亡焦慮」(death anxiety),驅使回顧罪惡。
從犯罪側寫看,歐陽吻合「變態反射」(perverse reflex):工作壓力誘發異常行為。 但同學的沉默(創傷後壓力)也間接反映案件的心理陰影。

綜合評估與啟示
歐陽炳強的心理圖像複雜:若為兇手,他是高功能反社會者(high-functioning sociopath),擅長掩飾;若無辜,他是韌性典範,冤獄未摧毀其意志。案件疑點(如纖維不全吻合)放大心理爭議:是慾望驅動的衝動犯罪,還是司法誤判的受害者? 心理學啟示:慾望壓抑易爆發,韌性可助生存卻也掩蓋真相。無論真相如何,這案提醒我們,心理剖析需謹慎,結合證據而非推測。

प्रतिबिंब
這是我的自白,完整版。從平凡到罪惡,從慾望到毀滅。記錄一個男人的墮落。希望讀者警惕:慾望如火,燒盡一切。
出獄後,我去跑馬地,重訪舊店。電車叮噹,路燈昏黃,像當年。但卞玉英的鬼魂,似乎還在閣樓徘徊。她的眼睛,永遠盯著我。
我後悔嗎?是的。但那興奮的回憶,偶爾還讓我顫抖。人生如夢,罪惡永存。